前言
當前胡適研究最大的一個盲點,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資料出現的情況之下,才可能會有胡適研究的新典範出現。殊不知現有的胡適資料,已經是浩瀚到沒有一個人可以全盤掌握的地步。研究胡適要面對這浩瀚的資料,固然是一大難題。然而,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要開創出新的典範,新的觀點才是法門。資料誠然是多多益善。然而,徒有資料,而沒有新的方法和觀點,是絕對不足以窺胡適的堂奧,更遑論要爲胡適畫龍點睛了。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一句至理名言。這種對資料的迷信,套用胡適在「問題與主義」論戰裡所說的「目的熱」和「方法盲」的話來說,就是「資料熱」、「觀點盲」。
我爲什麽會說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是「資料熱」、「觀點盲」呢?試看現在汗牛充棟的胡適研究的作品,不絕大多數都是在炒冷飯嗎?所有胡適一生中關鍵性的觀點、重要性的議題,哪一個人不是跟著胡適起舞、亦步亦趨?胡適說他從小偷讀傳統白話小說,奠定了他白話文的基礎;胡適說他八、九歲的時候,就能不怕地獄裡的牛頭馬面;胡適說他十二歲到上海去上新式學堂的時候,他的防身之具之一,就是「那一點點懷疑的傾向」;胡適說他從1915年的夏天發奮盡讀杜威所有的著作,說他的《嘗試集》的命名、《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寫作都是受到杜威思想的引導;胡適說「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說「杜威教我怎樣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胡適的實驗主義、自由主義、易卜生主義等等。所有這些,試問有誰去求證過?這就彷彿意味著說,只要胡適說過了就算數。
這種不思不想、胡適說啥就是啥的研究態度,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爲:「胡適說過就算主義」。我們且看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裡是如何抨擊「主義熱」的缺點:「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産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這幾句話說得多麽的重、多麽的斬釘截鐵、多麽的一杆子打翻船。這是論戰的語言,越猛烈越讓人叫好,而且也只有那後世皆曰「溫和」的胡適說了而人不以爲忤。其他人如果用如此激烈的話語來針砭社會,不被打成狂妄、偏激才怪。可是,這麽斬釘截鐵、一杆子打翻船的話,胡適說了,卻人人擊掌稱是。而且還禮贊他溫和、理性,凡事包容、不走極端、不事武斷。這原因無它,就因爲他是胡適。還有,因爲胡適罵的不是今天的讀者自己,而是從前的中國,以及可以用來影射的權威。言歸正傳,胡適說:「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把這句話拿來套用在當前的胡適研究,這種只管用「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來找資料的態度,便是「資料熱」;不管胡適說得如何?對不對?便是「觀點盲」。
這種「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上焉者就是照本宣科。胡適怎麽說,就跟著怎麽說。於是,所有描寫胡適的早年生活、他在上海上新學堂的經歷、他如何墮落、酒醉、到幡然醒悟而考上庚款留美的一切,也就是他《四十自述》的翻版。胡適留美的點滴、他爲什麽先念農學再轉哲學、他爲什麽公開演講、他的民主素養的訓練、他爲什麽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他爲什麽開始提倡白話文,所有這些種種,不外乎取材於他的《留學日記》、《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以及他晚年所作的《口述自傳》——而且用的還都是唐德剛錯誤頗多的中譯本。然而,這種研究雖然沒有新意,至少不望文生義、強作解人。而只是把資料重新整理一過,以胡適的自述作爲基礎,作補充的工作。
「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下焉者,就是「說文解字」式地把他的觀點拿來作爲臆測之資。林毓生把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視爲胡適不懂科學、犯了形式主義的謬誤、膚淺的鐵證,殊不知那根本就是19世紀許多科學、哲學家的共同看法,甚至是 1965年一位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說法。邵建批評胡適一定沒讀過洛克,所以不懂西方古典的自由主義。耿雲志看到胡適在《先秦名學史》的扉頁上說他這篇論文是「作爲博士考試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由於他不知道論文只是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諸多條件之一,於是他就望文生義地說這句話耐人尋味,等於是胡適暗認他博士學位只有一部分通過。劭建跟羅志田看到胡適1926年歐遊時稱讚蘇聯的話,就錯以爲胡適變得左傾。這類研究雖然有意對胡適的思想作詮釋、下批判。然而,由於它們所用的方法不外乎是就胡適來解胡適,用胡適自己的話作依據,而不是從杜威、赫胥黎、穆勒、易卜生等人的原作裡去追溯胡適思想的來源,不是把胡適放在他所處時代的思想脈絡下來分析,他們等於是墮入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周質平說胡適對「民主」有一個「簡明扼要」的「晚年定論」,那就是:「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就是承認人人各有其價值,人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發展。」周質平引的是胡適1955年所寫的一篇手稿:〈四十年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囯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
周質平這段話,就是「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裡閉門造車的典型,渾然不知胡適一輩子有他的「儻來主義」、偷關漏稅、引而不注的壞習慣。「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這句話根本就是杜威說的。而且連周質平所引的胡適對這個「生活方式」的詮釋,都完全是杜威所說的。這是杜威從19世紀末開始就常說的一句話。別處不說,胡適心知肚明的例子,就是胡適自己也參與撰文的杜威八秩祝壽論文集,亦即1939年出版的《老百姓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這本祝賀杜威八秩壽辰論文集的最後一篇,就是杜威的〈創造性的民主:我們當前的任務〉(Creative Democracy——The Task Before Us)。在這篇文章裡,杜威又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強調民主是一個道德的理想。他說:
民主作爲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相信人性。相信老百姓(the Common Man)是民主理念裡一個常見的信條。這個信條不會具有任何基礎和意義,除非我們相信人性的潛能以及每個人與生既有的能力……民主政治對人類平等的信念就是:不管一個人與生既有的能力如何,每一個人都有跟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去發揮自己的才能。民主政治所信奉的領導原則是相容並蓄的、是普及的,其信念是:只要環境對,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去引領他自己的生活,不受到他人的脅迫或強求。」
研究胡適,要能不墮入 「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要能不閉門造車,就必須要學習胡適所說的:要有「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態度。」胡適在世的時候,最喜歡勸少年朋友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說:「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因此,胡適喜歡教少年朋友學一點「防身的本領」。 這就是胡適要把「金針度與人」的道理。諷刺的是,要研究胡適,還得先學一點不被胡適牽著鼻子走的防身的本領。
這個用「一點點用功的習慣,一點點懷疑的態度」來作爲研究胡適的「防身的本領」是什麽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實實地去讀胡適所讀過的書。我們要知道胡適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不甚講究引注的時代,而胡適一輩子又有引而不注的壞習慣。最諷刺的是,胡適一輩子教誨年輕人寫文章的時候一定要注明完稿日期,以省後人考據的工夫。可是,比起別人不注明完稿日期這個小疵來說,胡適援引別人的書、文章、和觀點,而不加注腳,那才是累翻後人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出處的大愆呢!因此,要瞭解胡適思想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好好地去讀胡適所讀過的書,方才可以知道他許多思想的來源究竟如何。而且,也方才能知道胡適是儻來使用呢?還是後現代主義意義下的挪用?還是傳統意義下的誤用、甚至是濫用?
誠然,要去讀盡胡適所讀過的書是不可能的。這就好像要去盡讀胡適所留下來的資料、或者去看遍所有研究胡適的著作一樣,是會讓人興「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歎。這個難度只有真正去嘗試過的人才能領略到的。這是因爲胡適所讀過的書,中文的當然是難以盡數,英文的恐怕也至少成千。試想:光是胡適在康乃爾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選課所讀過的書就有多少,而這還不包括他自己課外所讀的書呢!
然而,在「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仍然充斥於胡適研究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先用戰略性地選擇閱讀影響胡適最深的一些作者的書,來作重點突破的工作。比如說,胡適說「杜威教我怎樣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然而,到底杜威怎樣教胡適思想,赫胥黎又怎樣教胡適懷疑?胡適從來就沒有清楚地交代過。他在世的時候,從來就沒有人要求胡適解釋杜威如何教他思想、赫胥黎如何教他懷疑。在他過世以後,也從來就沒有人對這句話作過質疑。「胡適說過就算主義」,莫此爲甚!這就是爲什麽我們研究胡適,就必須對胡適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原因。而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絕不能像從前的作法,貪圖撿現成地從胡適自己的文字裡去找答案。那種作法除了是緣木求魚以外,等於是自己套上牛繩,讓胡適牽著鼻子走一樣。唯一的法門,就是去讀杜威與赫胥黎的著作,然後再回過頭來審視胡適自己的文字,看胡適如何挪用、誤用、和濫用杜威和赫胥黎。
有多少人說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然而,有多少人能回答說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說法,是經過了他們研究分析以後所得到的結論?還是胡雲亦雲、人云亦云、想當然爾的結果?胡適有關實驗主義的文字,或者可以拿來作爲實驗主義的運用的文字,比比皆是。胡適到底是不是一個實驗主義者,或者究竟是什麽意義下的實驗主義者,我們都可以用這些現成的文字來作分析研究之用,不需要等新資料的出現。爲什麽胡適的研究到現在爲止沒有新的典範出現?「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使然也!
沒有人懷疑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然而,自由主義是一個空泛的名詞。套用胡適最喜歡說的話來形容,自由主義是一個籠統空泛的名詞。稱胡適爲自由主義者,就彷彿是說胡適是一個中國人一樣,沒有什麽詮釋的意義。更有甚者,說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套上了這個標簽,會讓人誤以爲那已經就是答案。其致命的結果是:說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本來應該只是一個研究的起點,然而卻因爲看起來像是一個結論,就被不假思索地引爲定論了。換句話說,用自由主義者來標簽胡適,其結果往往是把假設當作結論,那不但不能鼓勵人們去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而且適足以讓人畫地自限、從而阻遏了更活潑、更有創造性的分析與詮釋。杜威對這種標簽化的用語的批判就一針見血。用他批評「主義」的話來說:「這些觀念並不是爲解決特定的歷史問題而提出的。它們所提供的是籠統的答案,可是又自命爲具有普遍的意義,能概括所有的個別案例。它們不能幫忙我們從事探討,反而是終止了討論。」
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觀念,它是隨著時代的進展而被賦予新的意義的。18世紀的自由主義不同於19世紀的自由主義。胡適所處時代的自由主義也不同於21世紀的自由主義。隨著社會經濟的情況的變化,全球化經濟的擴展,自由主義的使命也必然要與時俱進。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問胡適是在什麽意義下的自由主義者。我們更必須要問以杜威的弟子自居的胡適,究竟是如何詮釋、挪用、或誤用杜威的自由主義?
同樣地,胡適那膾炙人口的〈易卜生主義〉已經是將近一個世紀以前所寫的文章了。〈易卜生主義〉不但使「娜拉」、「斯鐸曼醫生」成爲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階級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甚至影響到近代中國對易卜生戲劇藝術的接受與瞭解。可是,有誰曾經好好地去讀易卜生的劇作,看看胡適所最愛徵引的《娜拉》、《國民公敵》、《群鬼》、《雁》、《社會的棟梁》、以及《我們死人再生時》到底都寫的是什麽?胡適究竟是選了易卜生戲劇的什麽部分來詮釋易卜生呢?爲什麽胡適會作那樣的選擇呢?胡適把易卜生引介進中國,誠然有功。然而,他的詮釋是否把易卜生的戲劇藝術貧瘠化了,從而局限了中國人對易卜生戲劇藝術的理解呢?
胡適不但是一個歸國留學生,而且他一生有25年是在美國度過的,超過他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時光。從這個意義來說,美國等於是他的第二故鄉。這第二故鄉的意思,指的還不只是他住的時間長而已,而且是指他的心態、他的思想方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裡提到有名的中日古典文學名著翻譯大家英國人韋利(Arthur Waley)。韋利說胡適雖然形體上是中國人的樣子,他根本等於就是西方人。我在本部還會提到一個美國學者,他說胡適寫起英文來,行文立論根本就是美國人的樣子。
我們要如何來研究一個在長相上是中國人、但在思想上是西方人,寫起英文來,行文立論根本就像是美國人的胡適呢?如果我們對杜威、赫胥黎、易卜生的瞭解不超過胡適,或至少要能夠跟他平起平坐,我們就沒有資格研究胡適。如果我們對胡適深愛到至死不渝的美國的歷史、社會、政治、與文化不超過胡適,或至少要能夠跟他相侔,我們就沒有資格研究胡適。如果我們對胡適所讀過的重要的著作,沒有嘗試去閱讀,或至少是涉獵,我們就沒有資格研究胡適。
這完全不意味著我們要跟胡適比賽,看誰的學問好,更不是要證明胡適的「膚淺」。事實上,所有「胡適膚淺論」,可以休矣。所有「胡適膚淺論」都屬於一種飛去來器(boomerang),最後擊中的都是說胡適膚淺的人自己。我們要沉潛地去讀胡適讀過的重要著作,只不過是要超越「胡適說過就算主義」,是要老老實實地爲研究胡適作準備的工作。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裡說:
在胡適出生百年後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適「膚淺」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過是學術的漸進,而不是嘵嘵然貶抑胡適者個人的聰明與才智;反之,在胡適出生百年後的我們,既有坐擁群書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裡,隨時手打鍵盤,上圖書館期刊網搜索、閱讀論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適,則該汗顔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樂道地細數胡適的「膚淺」。
同樣地,我在《舍我其誰》裡批判歷來研究胡適的錯誤,也不是在跟研究胡適的學者比學問的高下。學術的進步,端賴於學者之間的腦力激蕩。學者腦力激蕩的場所無它,就在學術著作裡。現代學術研究的規範爲什麽有引注的規定呢?這個最低的要求,自然是規定學者必須有引必注。更重要的——而這也是學術研究所賴以進步的引擎——就是要求學者必須參考歷來研究的成果。作研究如果不征不引、不去檢視既有的研究成果、不與其他研究者進行問難,那就只是閉門造車,彷彿自己是開天闢地第一個研究的人。這種學風不但不負責任,而且有礙於知識的積累、創新、與突破。研究者必須參引既有的學術研究成果,爲什麽贊同?爲什麽質疑?有什麽更好、更合理的詮釋?只有在這種腦力激蕩之下,學術才可能日新月異,精益求精。
現代社會分工精細,
宿業有專攻。俗話說得好,隔行如隔山。不是人人都有時間、精力、與素養從事學術研究。學者得以專心從事研究、撰述、出版,端賴社會的供養、社會資源的享用。學者對社會的回饋,就是在腦力激蕩所在的著作裡,注明他們的所征、所引、所依、所違、所惺惺相惜、以及所推陳出新之所在。這不是爭勝,而是基本的學術研究的規範,更是研究者對學術與社會的責任。這絕不是在賣弄、掉書袋,而是在讓讀者知道論述的所據、其來龍去脈,以作爲衡量、評判、並決定接受與否的根據。
陳毓賢在《東方早報》上爲《璞玉成璧》所寫的書評裡,承認我「能用新的眼光審視胡適,替胡適研究帶來新氣象。」然而,她批評我有「走火入魔」的危險。她說:「可是寫胡適傳若存心要解構,則怕應了英語一句俗語:『你手裡握著鐵錘,就到處看到釘子。』」這是一句英文的俗諺:“When you have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這句話更傳神的翻譯是:「對手裡握著鐵錘的人來說,凡事看起來都像是該被敲平的釘子。」其實,這句話還有另一層的寓意:「手裡握者鐵錘的人,總以爲那是解決萬事的法寶。」她說: 「胡適的傳……若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他能掌握的資料加以整合,已是傳世之作。」
我在新出版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增訂版)》的〈前言〉裡有幾段回應陳毓賢的話。我知道有些讀者認爲那是一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有關「個人隱私」的作品,不屑一讀。其實,研究的議題無分高下、公私、與本末,所有的議題都值得研究。研究的好壞,端賴於作者的觀點與功力。只要方法好、資料對、觀點新,則靈。點石成金,固然是煉金術的範疇。然而,學術研究,也大可以把那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資料,點石成金,成爲灼見的依據。所謂見微知著,亦學術研究的蹊徑之一。無論如何,我把我對陳毓賢的回應放在這裡,冀望能得到被更多讀者檢視的機會。
陳毓賢所謂學術研究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來作整合的工作云云,是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paradigm)以前的思維方式。孔恩這「典範」的觀念,胡適其實也有與它暗合的想法。胡適從整理國故的經驗裡所悟出來的道理,就是孔恩「典範」的真諦。他在1920年代初期研究《詩經》的時候,感歎說:「二千年的『傳說』(tradition)的斤兩,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把這個胡適研究《詩經》的感歎拿來用在胡史研究的領域,也完全適用。一個世紀以來的胡適研究的「傳說」,包括胡適自己所建構出來的「傳說」,恐怕也何止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
從胡適的「大力漢」、孔恩的「典範」以前的思維方式來看,知識是成直線積累的。因此,新、舊「出土」的資料,可以像混凝土一樣攪拌起來,就彷彿雞鴨同鍋可以烹製出一道絕品佳肴一樣。殊不知世界上沒有什麽資料是可以「出土」而現成可用的。這又是中了那19世紀實證主義思想的餘緒而不自知。試想:連所謂「出土」的文物,都須要經過鑒定與詮釋以後才能成爲「文物」,文字的資料如何能自外於鑒定於詮釋的程序呢?所有的資料都是詮釋的産物。在沒有透過詮釋而賦予意義以前,「資料」等於是不存在的。杜威說得好:那些在山上岩石裡的鐵礦石,毫無疑問地,是「粗獷的素材」。但在人類發展出技術把它們提煉成鐵以及後來的鋼以前,它們的存在對人類並不具有任何意義。在那個時候,鐵礦石跟其他岩石並沒有什麽不同,都只是岩石而已。換句話說,只有在人類發展出煉鐵技術的脈絡之下,鐵礦石才被人類賦予了新的意義。
從胡適的「大力漢」、孔恩的「典範」以前的思維方式來看,「新」典範的建立者看起來不是張牙舞爪,就是無事忙。陳毓賢說我吹毛求疵、多臆斷、好擡杠,只可惜她完全沒舉證說明。在她眼中,「新」典範的建立者儼然是因爲手中握著一個大鐵錘,不用白不用,於是四處找釘子敲。殊不知他們手中即使有著那麽一個大鐵錘,他們所要敲的還輪不到那些凸出來的釘子呢!那些釘子全都要重新鑄造過以後才能再用!
「大力漢」手中的那把鐵錘,不是要大材小用地拿來敲釘子用的,而是拿來摧枯拉朽用的。敲打釘子,等於是在那「舊」典範裡作補苴罅漏的工作。試想:如果不拿那大鐵錘來作摧枯拉朽的工作,何以能有另辟蹊徑、重起爐竈的可能?那大鐵錘揮舞起來固然看似破壞;那大鐵錘揮舞起來,看似不知感恩「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道理。但這是新、舊「典範」交替的自然過程,就像留學時期的胡適所說的:「死亡與凋謝,跟新生與成長,同樣是有機的演進裡必要的過程。」那眼前看似張牙舞爪的新典範,不消多時,就會變成衆人皆曰是的「典範」。然後,等那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新典範崛起以後,這也曾經「新」過的典範,又會成爲被摧枯拉朽的物件。
胡適是一個天才。然而,說他是天才,只是一個事實的陳述,並不意味著褒或捧的意思。同樣地,即使我在本傳裡對胡適批判的地方所在多有,那也不意味著貶或抑的意思。研究胡適的目的不在褒貶胡適,更不在把胡適拿來作爲針砭或借鑒之用。任何研究都必然會反映其時代的價值、思想、與氛圍。不只是意識形態,連用字遣詞都是時代的産物。這不只在意識形態經過戲劇性變化的中國是如此,即使在美國亦然。一本2010年代所寫的書,其行文立論必然迥異於1950年代所寫的書。時代如此,個別作者亦然。任何研究都必然反映了作者的立場、學識、品味、與意識形態。然而,時代的印記跟作者的立場,就好比像酒的色澤、味覺、和餘味是由葡萄的品種、産地、天候、釀酒師、和酒廠等等因素來決定的一樣,那個別的特色是就是釀酒藝術的結晶。
相對地,把胡適拿來作爲針砭或借鑒之用,就不是在研究胡適,而只是借胡適來抒發個人的政治理念。這種「研究」,不管是影射史學也好,指桑駡槐史學也好,胡適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就好比同樣是釀酒,人家釀酒大師釀的是醇酒,他釀的則是藥酒;釀酒大師釀的酒是品嘗用的,他炮製的酒則是補腎用的。這其間分殊的所在不可等閒視之:品酒者,不乾杯;釀酒大師,不釀藥酒。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胡適研究平添了兩個極有意味的因素:一個是翻案平反的熱切;另外一個是對政治思想牢籠的反動。由於從1950年代清算胡適鬥爭到1980年代改革開放爲止,胡適一直被打成一個負面的人物,翻案平反很自然地就成爲改革開放以後胡適研究的主流。隨著思想空間的擴大,翻案平反之風,又與對政治思想牢籠的反動合流。在翻案風的推波助瀾之下,胡適與魯迅儼然成爲對比的樣板。於是,各種光怪陸離的胡適與魯迅的對比都出籠了。例如:魯迅是酒,胡適是水;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魯迅是閃電,胡適是陽光;魯迅是姜湯,胡適是可樂;魯迅是黃河,胡適是長江;魯迅是把手術刀,胡適是片止痛藥;魯迅是一道溝,胡適是一座山;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等等、等等。這個對比的名單可以無窮的延伸,一直到人們的想象力用完爲止。這彷彿是說胡適與魯迅,非此即彼,兩者不能並存、或相得益彰一樣。殊不知不管是揚胡抑魯、抑或是揚魯抑胡,作爲二分法、作爲樣板,其異於從前不黑即白、不左即右的思想模式幾希?
崇拜胡適的人形容胡適爲中國現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爲未來中國的指標——所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說法——則是把歷史與未來混淆了。毫無疑問地,不懂得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人,不愚即妄。然而,所有想象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人,都必須先牢記住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裡所說的話:「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産兒。」所有的學說「都只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生吞活剝、盲目亂抓藥,是一大忌。換句話說,胡適本人以及胡適的思想是他所處時代的産物。活在20世紀前半葉的胡適,如何可以作爲21世紀的領航人呢?這根本就跟胡適——其實是杜威——處處對人諄諄善誘的道理是背道而馳的。 杜威在胡適所熟讀的《實驗邏輯論文集》裡說得再清楚也不過了:
所有解決、診斷具體情境的方法,從某個角度來說其實都是未完成、未解決的。每一個這種情境都是特殊的。它不只是未完成的,而且其未完成的情況也是那個具體情境所特有的。
由於每一個情境都是特殊的,每一個時代都是不同的,所謂歷史的教訓,都是經由經驗的累積與智慧的判斷的結果:
我們經過深思熟慮以後所作的抉擇,是建立在從前類似的情境之下所作的抉擇的基礎上的。當研究得到了結果,而且結果也驗證了結論以後,其結果就被傳承下來。類似的情境會重復出現。在某種情況之下,甲法優於乙法。可是在另一種情況之下,甲法又劣於丙法,等等,等等。成例於是産生。我們所屬的社會必須在許多方面,都有類似的經過思考過後所産生出來的成例。我們所看重的或那些有價值的成例,在日後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的時候,就儼然成爲「天經地義」(facts)的標準。同樣地,從前評斷過程中一再出現的事物也變成是普世的價值。
然而,杜威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是日新月異的。從前適用的,今天就不見得能適用。同時,就是從前所適用的方法,我們也必須去追問其效果是否經過了嚴密的檢證:
我們必須瞭解這些價值和標準都只是待證的假設。在一方面,它們是否有用,完全要看目前的情況是否和從前相同。在今天這個進步、變化急劇的社會裡,這種可能性是大大地降低了。我們如果不懂得以古爲鑒,那笨的是我們自己。然而,我們必須要注意:習慣很容易讓我們忽略了異,而假定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同,因而作了錯誤的判斷。在另一方面,成例的價值,端賴於其是否是批判性地取得的。特別重要的是,其結果是否經過嚴密的檢證。換句話說,成例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它是否經過嚴格的檢驗過程。
杜威這段話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所含蘊的智慧:歷史可以作爲借鑒,可是未來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去創造。如果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那就意味著中國人雖然是活在21世紀所特有的具體環境裡,卻要倒退一百年,去思那早已事過境遷的胡適之所思。事實上,胡適的思想的基調,用我在本部《日中當中》的分析來說,是維多利亞後期的思維。如果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的話,那未來的中國就要回到19、20世紀之交。這是科幻小說裡的時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屬於嚴肅思考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的範疇。
胡適不求涅磐,也不盼望天堂。他從杜威那兒所學到的,就是從具體的情境去求取那一點一滴的進步。雖然實驗主義是展望未來、以未來作取向的,但那未知的「未來」從來就不是胡適措意的所在。胡適的人生哲學是好好地、努力地活在當下。我在《璞玉成璧》裡提到了他的好友丁文江的座右銘:「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我說只有像丁文江、胡適這樣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才能真正體會到讀書、作事要像「人可以長生不老」、品嘗人生要彷彿「人沒有明天」的真諦。只有像胡適與丁文江這樣的人,才能真正領會到布朗寧所說的「再蹶能再起、憩息以復蘇」的精神。胡適說:「不作無益事,一日是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他拚命做工,一日是三日,因爲他要向世人證明:」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
《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9-1927》能在一年當中寫成,完全是拜休假一年之賜。我能有幸得到這一年不需要教學,而得以專心寫作的機會,一方面要感謝我任教的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所提供的一學期得以休假從事研究的「費雪研究獎金」(Fisher Fellowship);另一方面更要誠心感謝臺北的陳宏正先生,在慷慨資助我寫完《璞玉成璧》以後,繼續慷慨資助,讓我得以用一年的時間全力完成《日中當中》的寫作。
我身在美國,任教大學的圖書館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如果不是因爲「胡適檔案」已經掃描存檔,而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經把它公佈在網站上提供學者自由使用(可惜現在又不對外開放了) 我研究胡適的計劃就絕對不可能進行得如此順利。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胡適紀念館前任館長潘光哲先生的鼎力支援、現任館長雷祥麟先生立時批准我授權使用胡適照片的申請、鄭鳳凰小姐細心地幫我提調、查考檔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楊貞德小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的崔祥蓮小姐、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文庫的鄒新明先生,每次在收到我告急求援的電郵,都慷慨熱誠地幫我查找資料、掃描,不勝感激。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妻子麗豐,謹獻上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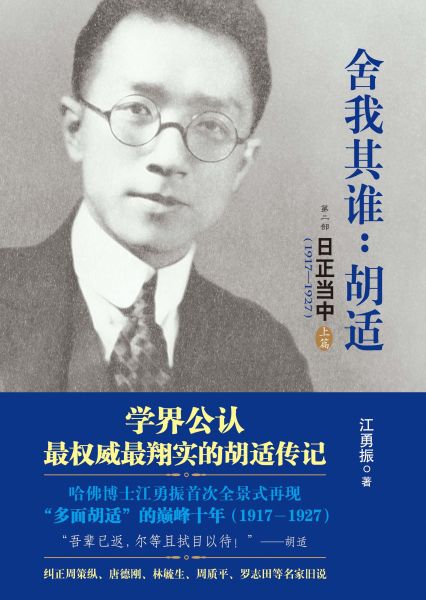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