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9冊2004年的文集,還列出數十篇"未收作品存目",很有意思。
天津百花出版社的九卷本《余光中集》不收〈胡適:中國的良心〉。
---
將作家余光中詩作介紹到中國大陸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余光中「光大了中國詩,他對得起他的名字」。流沙河回憶,余光中從不說別人不好,被罵也不還口,「這樣的作風,我小時候在『舊社會』見過。」流沙河今年86歲,是.... – rti.org.tw
最先是阿邦告訴余先生的死訊。
我這幾天忙著準備胡適之先生紀念及其他主題的slides等,只簡單地說:90歲了。前幾周,無意間將百花文藝的余光中集十冊取出,還來不及看。
後來,跟一位朋友說,"你有點偏見。雖然近年少看他的作品,其質量還很可以 (當然他為馬英九作Bumbler解釋,發揮"御用作家"的一點娛樂作用)。......
如何評價某一作家,很容易有意氣。某位朋友看了高行健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大失所望。我說看看他的長篇吧。在80年代初,我也有朋友不喜歡余先生的詩譜成的"校園民歌"。
我一直是上班族,讀書範圍廣,沒特別意見/喜好,還有許多書或電影等待讀。.....余先生的文章都有點巧思,然而不至於讓我很感動。
我這幾天忙著準備胡適之先生紀念及其他主題的slides等,只簡單地說:90歲了。前幾周,無意間將百花文藝的余光中集十冊取出,還來不及看。
後來,跟一位朋友說,"你有點偏見。雖然近年少看他的作品,其質量還很可以 (當然他為馬英九作Bumbler解釋,發揮"御用作家"的一點娛樂作用)。......
如何評價某一作家,很容易有意氣。某位朋友看了高行健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大失所望。我說看看他的長篇吧。在80年代初,我也有朋友不喜歡余先生的詩譜成的"校園民歌"。
我一直是上班族,讀書範圍廣,沒特別意見/喜好,還有許多書或電影等待讀。.....余先生的文章都有點巧思,然而不至於讓我很感動。
----余光中當時是後輩,不懂得稱" 胡適之先生"。
余光中談胡適:中國的良心
2019-02-28 20:5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適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 我的敵人胡適之”和“ 我的朋友胡適之”同樣流行於中國的文化界。一個手無寸鐵的學者, 竟能造成舉國友之甚至舉國敵之的局面,在現代中國,還是絕無僅有的例子。事實上,才高於胡適者有之,學富於胡適者有之,國際聲譽隆於胡適者有之( 如林語堂及李、楊)。然而胡適在中國文化界何以如此重要呢?此無他,胡適是思想界的一個領袖,他言行一致,貫徹始終,而且用極其淺近明暢的白話來表達他的思想。胡適何適?他以古稀之年迢迢來歸,雖然在學問上並無滿意的成就,總算把這把老骨頭光榮地埋在這座孤島上。
胡適已經死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親痛仇快,棺已蓋而論未定。我敢相信,歷史的定論將是正面的。胡適是現代中國自由思想的領袖,也是現代化運動的一大功臣。沒有胡適,我們眼前偏見之霧將更濃。沒有胡適,我們和民主的距離將更遠。沒有胡適,我們的教育將更不現代化,更不普及。時至今日,我們最需要的仍然是科學與民主,因為科學並不等於原子爐或電視,民主也並不等於選舉或罷免。有人斤斤計較,要憑信史溯五四運動之源。事實上這於胡適有何損?可貴的不是誰先創始,而是誰最堅持不移,誰最具影響力量。
胡適的影響遍及整個文化界。此處我想縮小範圍,僅論其文學的一面。在這方面,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罵胡適的人,必須用白話文,才能使別人了解。胡適鼓吹白話文學, 使文字與語言再度結合,乃年輕了久已暮氣沉沉的中國舊文學。此舉可以比之歐洲的文藝復興和華茲華斯的反古典運動。然而胡適在中國文學的地位並不足以比擬但丁或華茲華斯。本質上他是一個改革家、運動家,不是一個作家。
固然,他也寫新詩和散文,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思想傳達的成分仍濃於藝術的創造,亦即說明多於表現。他主要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新詩充其量像愛默生或梭羅的作品,但缺乏前者的玄想及後者的飄逸,不,有時候他的新詩只是最粗淺的譬喻而已: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像這樣的一首詩,在藝術上的評價實在很低,儘管它可以被引用來印證胡適的思想或人生態度。胡適在詩中用了一點起碼的象徵,可是這種象徵是淺近而現成的,不耐咀嚼, 像是蓋在思想上的一層玻璃,本身沒有什麼可觀。又如下面的一首:
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
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溫舊夢。
其中的措辭與節奏,實在都是陳舊的,最多只是較自由的舊詩。事實上,五四時代的新詩人們,雖然有志推行新詩運動,但一方面由於對舊詩欠缺透視的距離,對西洋詩尚未認識清楚;而另一方面,以白話為基礎的新語文尚未演變成熟,是以當時的新詩只是半舊不新的過渡時期的產物,做文學史的數據則可,做美感的對象就勉強了。一直要到徐、何、卞、李、馮、戴1諸人,新詩才算進入美的範圍。
是以五四的新詩運動,本質上是語言的,不是藝術的,而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historical ),不是美學的( aesthetic )。在今日的台灣,幾乎任何新詩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嘗試集》。可是文學是漸漸發展而成的,不是無中生有的,沒有胡適的努力,怎能有今日的自覺與成就?反過來說, 置我們於五四時代,我們的作品也許還不如《嘗試集》。何況胡適的活動初不限於新詩一隅,他的成就是全文化的。
無疑地,胡適先生sic是一個偉人。可是過分崇拜偉人和盲目詆毀偉人,是同樣地有害的。偉人而成為偶像,則其偉大性已經變質,於本人、於社會,都很不利。攻擊胡適者,動機複雜,風度各異,不必詳述。但是“ 捧”他的人有時也未免過分了。把他的新詩登了又登,把他的隻字片言當作廣告利用,把他的逸事傳了又傳,甚至譽他為大詩人、大作家, 甚至推他去應徵諾貝爾獎金( 雖然比推別的一些人要切題得多),就似乎“ 走得太遠了”。而胡先生本人呢,在文學欣賞上,如果不是不夠深刻,至少也是相當隨便。
例如對於某些小說,胡先生實在不必捧場。在胡先生不過是聊表鼓勵,甚至不願掃興,可是一言既出,為天下法,就苦了那些“ 愛好文藝”的中學生了。胡先生的毛病,在於對文學的要求僅止於平易、流暢、明朗。這要求太寬了、太起碼了。這些性質原不失為文學作品的美德,可是那應該是透過深刻的平易、密度甚大的流暢、超越豐富的明朗。胡先生的散文實優於詩,他的譯文也很清新,只是他的散文仍是思想家的散文,宜於議論,不宜於把握美感經驗。
然而胡先生畢竟是民主的鬥士、思想的長城、學界的重鎮、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敲打樂器、新文學運動的破冰船。和這種人同一時代是幸運的,也是光榮的。我也曾有過罵他的衝動,直到去年春天,在一個可紀念的場合我見到了他,見到了他那自然而誠懇的風度,我很感動。我為他的死難過。
中國的苦難正深,偏見猶濃,胡適死了,民族的良心將跳得更弱。可是,當一個軍閥、一個政客死時,他是完完全全地死了;當一個真正的學人死時,正是他另一生命的開始。
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六日
本文摘自《左手的繆斯》,余光中 著,聯合讀創 出品,2017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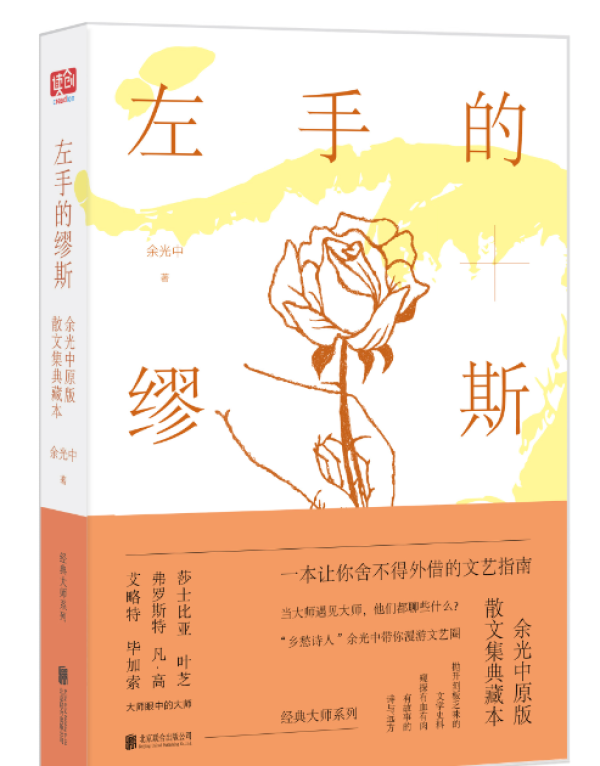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學者、翻譯家,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被譽為文壇的“璀璨五彩筆” 。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
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胡適死了。對於中國的文化界說來,這是異常重大的損失。對於胡先生本人來說,我毋寧慶幸他死得其所。在動蕩的中國文化界,能像胡先生這樣忠於自己的信仰且堅其晚節的學者,太少太少了。在今日的台灣,罵胡適是一件最安全的出風頭的事。有人說他對大陸淪陷應該負責,有人說他是中國人的恥辱,有人罵他是學閥, 有人甚至主張把他空投大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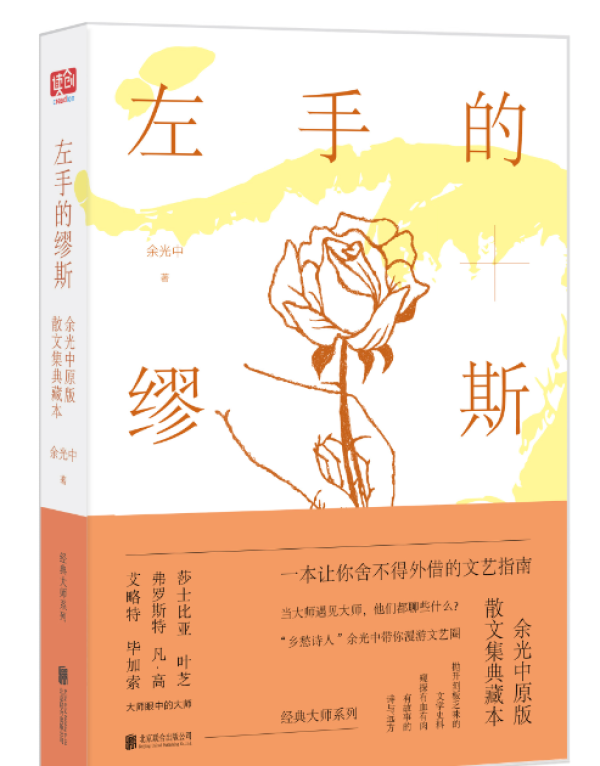
關鍵詞>> 余光中,胡適,文化,歷史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